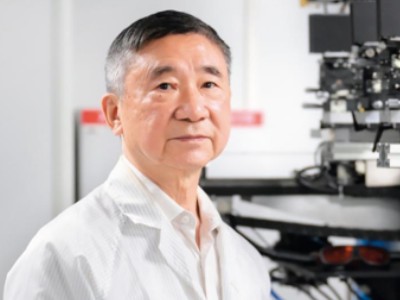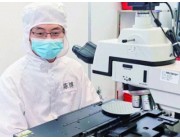最后想說的是,因為近幾年的國際形勢,大家明顯感覺到供應鏈存在一些危機。在國產替代的趨勢下,國內對國產的芯片、傳感器支持力度不斷提升。
其實之前的傳感器產品幾乎都來自國外的傳感器大公司。這些公司大多以IDM模式運營,有很多大規模的Foundry廠,同時他們有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和技術積累,在競爭上的技術優勢和價格優勢上足以筑起一道厚重城墻,將后來者擋在行業的大門外。
所以,國內芯片危機和自主可控的雙重影響,給國內企業帶來了產業機會。可以看到現在國內的一些客戶在積極的使用國產傳感器。
這些痛點如何破局?從睿感這塊的來說,雖然我們的產品技術全球領先,但我們的供應鏈也會有風險。比如我們也會缺一些最基本的輔助性材料。綜合來說,傳感器產業鏈的建設非常關鍵,不管是產品能夠設計出來,還要能生產出來、代工出來。這一塊的話,因為睿感成立背景比較特殊,我們也會在在合規的情況下,盡可能的把研發、制造等環節慢慢的移到國內來。
“通過收購、并購的方式,可增加協同效應。”
Q:請您談談在缺芯、本土化供應鏈安全和半導體投資熱潮這樣的大背景下,傳感器企業如何“謀變”?
鄧川軍:單從市場規律來看,國際上發展比較好的傳感器公司有TE、霍尼韋爾、TDK等。可以看出他們的發展壯大也是通過不斷的收購、并購來實現的。
因為傳感器的門類特別多,公司不可能做到每個產品都去開發,投入產出比低。通過收購、并購的方式,可增加協同效應。比如在共性平臺既可以生產加速器,也可以生產陀螺儀等其他產品,這樣整個平臺使用率更高。對客戶群來說,平臺可銷售多類傳感器產品,客戶使用起來也比較方便。
所以睿感目前要做的是提升現有的業務,首先是結合國內發展需要或投資人策略,爭取打造成一家傳感器的平臺公司。以現有的產品為基礎,將整個客戶群、供應鏈、制造技術整合在一起。在這基礎之上,我們再來做技術開發。第二是看到比較好的標的,我們將其整合,形成一個多品種、多產品線的傳感器公司,形成規模效應。
另外,傳感器的開發與傳統的數字芯片不同,其工藝中涉及到機械類、化學類、物理類等制造內容,需要不斷的調試、改進。舉個做菜的例子,都是同樣的原材料,為什么做出來的菜品有好有壞呢?原因是這里面有很多的配方。
比如IDM的模式運營的好處是設計好產品可以立刻去調試、改進,減少溝通和時間成本,加快整個產品的開發過程。這對MEMS傳感器公司來說是很好的商業模式。
Q:睿感未來會朝著什么樣的商業模式運作?
鄧川軍:我們現在是Fabless模式,共性的產品技術工藝,可以放在代工廠去做,但關鍵的工藝技術,比如CMOS、MEMS尤其后道處理的工藝,我們都希望掌握在自己手里。這樣做的好處也可以開放給國內有同樣需求的傳感器廠家,極大的提升整個國內的MEMS制造水平。
因為傳感器里面有兩個單元,一個是MEMS傳感單元,另一個是ASIC單元,將這兩個die進行bonding,通過SiP技術將他們合在一起的。我認為下一步的工藝就是MEMS和CMOS單芯片的技術,可以整合在同一個die上面的,這樣整個產品成本更低、體積更小,這是我看到比較好的趨勢。
所以,我們的戰略方向是打造成一個傳感器平臺公司,這個平臺不僅可以自用,也可以支持我們的合作伙伴和同行不斷發展壯大起來。未來有機會通過整合與合并,發揮規模效應、整合效應。
Q:各行各業談產業發展和進步總離不開人才創新。請您談談當下傳感器行業人才培養和創新困境?該如何彌補?
鄧川軍:真正做傳感器的公司確實沒有那么多,可以看到傳感器行業人才很匱乏,特別是從事技術研發的人才。目前傳感器人才可能更多的是聚集在在科研院所、高校里。但科研院所和高校工作模式區別于產業界,更多的可能以課題、報告的形式更多一點。所以產業界和學術界要緊密的配合起來。
睿感這塊也是同樣如此,我們也在跟科研院所、高校等建立聯合實驗室,共同去做一些相關專項課題。通過和學術界的互動交流,形成優勢互補,推進更多創新技術加速轉化落地。
另外,在人才培養方面,睿感也在積極計劃將優秀人才派往國外,通過學習、吸收和消化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帶到國內推動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