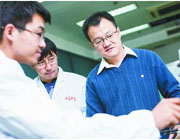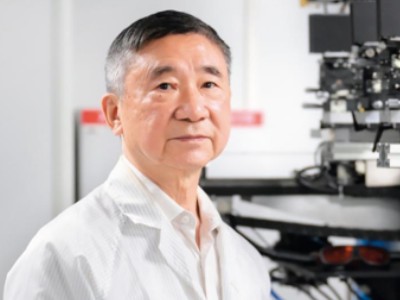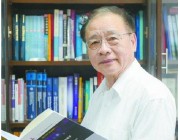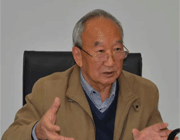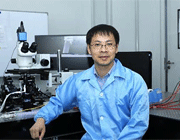過去百年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所涉及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和重大發(fā)現(xiàn)中,近70%借助儀器完成,物理和化學領域的發(fā)展更是離不開科學儀器的支撐。
正是意識到儀器在促進科技進步、推動人類認識客觀世界方面的重要意義,十多年來,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杜江峰帶領的微觀磁共振重點實驗室團隊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長期支持下,“邊科研邊研制”,在微觀尺度磁共振譜學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創(chuàng)成果,60余篇相關論文在《科學》《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評論快報》等期刊上發(fā)表,多項成果獲得獎勵。他們依托創(chuàng)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種儀器,已廣泛服務于高校、研究所、醫(yī)院和企業(yè)。
杜江峰認為,如果研制出原創(chuàng)的科學儀器是從“0”到“1”,那么把儀器送到千萬用戶手中,讓用戶來驗收就是從“一”到“萬”。在當前中國急需各種高端儀器的情況下,儀器研制應做到從“零”到“萬”。

杜江峰(右)指導學生做實驗。
“借”和“買”的困境
上世紀末以前,我國科學家多數(shù)是做些不用儀器或使用低端儀器的研究。后來能從國外買一些高端儀器,但不少研究仍是“買得到就做,買不到就不做”。
“這給科技創(chuàng)新帶來了巨大阻礙。一是發(fā)達國家對高端儀器禁運,有錢也買不到。二是即便能買,拿到儀器時也比人家晚一個階段。三是拿到儀器后,因為沒有維護維修能力,往往難以發(fā)揮最大作用。”杜江峰對《中國科學報》說,“現(xiàn)代科技已經(jīng)發(fā)展到高度依賴尖端科學儀器的階段,但我們的供給嚴重不足,儀器缺乏已經(jīng)成為制約我們原始創(chuàng)新的大問題。”
20年前,杜江峰團隊基本上靠借儀器做實驗,聽說哪里有儀器,就跑去測一測,做個實驗。10年前,團隊有了第一臺進口儀器,利用那臺儀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發(fā)了文章。很快,“借”和“買”都不能滿足需求了,他們就萌生了“自己做儀器的想法”。
2010年,團隊得到中科院支持,啟動一個200多萬元的儀器研制項目。通過那個項目,團隊積累了研發(fā)經(jīng)驗,也得到了鍛煉。
隨著國內科學研究對儀器的需求越來越旺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科技部、財政部陸續(xù)推出一些儀器研制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國家重大科研儀器研制項目定位于“前端”和“創(chuàng)新”,項目承擔者需要做出從“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創(chuàng)的儀器。
“我們去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科研儀器研制項目時,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礎,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還有一支優(yōu)秀的團隊。”杜江峰說,“當時我們提的方案合理,各項指標也非常高,國際上又沒有同類型儀器,這完全符合項目定位。”
“多波段脈沖單自旋磁共振譜儀”能夠在不破壞研究對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觀物質內部結構信息,拓展人們駕馭單個核自旋的能力,對前沿基礎科學以及提升我國開展原創(chuàng)性研究能力意義重大。
2013年初,杜江峰團隊順利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家重大科研儀器研制項目資助,團隊成員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番。
蓄積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儀器之“痛”有兩個突出表現(xiàn)。一是發(fā)達國家的技術封鎖,有錢也買不到。二是當我國少數(shù)領域邁入國際前沿時,迫切需要的儀器國際上也不一定有。
當中國科學家在多個領域躋身國際前列時,缺“儀”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轍。
在研制多波段脈沖單自旋磁共振譜儀時,有個關鍵部件叫鉆石傳感器,它的靈敏度決定著儀器的性能。但當時相關的原理才提出來四五年時間,國內外都沒有現(xiàn)成的設備可參考。
“當時美、德有個研究組也在往這個方向走,知道我們要研制后,馬上把相關的技術和產(chǎn)品都封鎖了。”該團隊成員、中科院微觀磁共振重點實驗室副研究員王鵬飛說,“國外廠商禁運了鉆石傳感器相關的產(chǎn)品和技術,所以一開始,我們就面臨很大的困難。”
鉆石傳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種離子注入技術,但當時大家連離子注入的機制都不清楚。
“杜老師在理論上給予指導,和我們一起討論,研究解決方案。”王鵬飛說,“我們從一臺農(nóng)業(yè)育種注入機上得到啟發(fā),對它進行改造和設計,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終達到了項目初步目標。”
后來,團隊不斷摸索,找相關單位攻克VR加工技術、波導設計加工工藝。經(jīng)過幾輪迭代,團隊用不到3年時間,將鉆石傳感器技術提升至國際先進水平。
“2016年底,連傳感器的原料也被發(fā)達國家禁運了,我們必須一點點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藝難關,但這也讓我們一步步、全鏈條地掌握了核心技術。”中科院微觀磁共振重點實驗室副研究員秦熙說,“在這個過程中,能明顯感覺到國外儀器廠商對我們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幾輪反轉。”